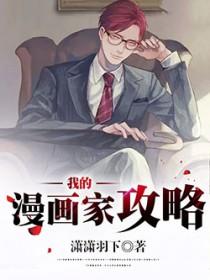盗墓小说>港娱:开局被解约的我成了幕后大佬 > 第10章 五成(第1页)
第10章 五成(第1页)
顾远一个人时,住在哪儿其实无所谓,一张床,一张桌子,能遮风挡雨就行。但现在多了个李晓红,再挤在那间只有二十平米、昏暗潮湿的出租屋里,就显得有些局促和不便了。
尤其对李晓红来说,一个女孩子,天天打地铺也不是长久之计。顾远看着她每天小心翼翼地在狭小的空间里活动,尽量不打扰自己工作的样子,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。更何况,他接下来的计划,需要一个更稳定、更像样点的“根据地”
。
指望申请公屋?顾远摇了摇头。他这种无根无底、职业定位模糊(在别人看来)的“艺术工作者”
,在八十年代的香江想排上公屋,那得等到猴年马月。
好在,豹哥那两万块“定金”
及时送达。钱不算多,但解了燃眉之急。
顾远不是个会委屈自己的人,尤其是在有条件改善的情况下。他很快就在观塘工业区附近,找到了一个相对宽敞些的单位。四十平米,一室一厅的格局,虽然依旧是老旧唐楼,但胜在空间大了近一倍,采光和通风也好上不少。至少,李晓红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间,不用再睡客厅地板了。
房东是个典型的香江师奶,精明,嘴碎,但也讲究实际。一开始自然是讨价还价,把租金咬得死死的。
顾远也不跟她磨叽,直接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钞票,不多不少,一万块。
“五个月租金,一次付清。”
顾远语气平淡,仿佛在谈论今天的天气,“如果可以,我现在就签合同。”
房东太太看着那叠厚实的“大牛”
(五百元港币),眼睛都亮了。这年头,肯一次性付几个月租金的租客可不多见。当下态度就软化了不少,嘴里说着“哎呀,靓仔你这么有诚意,那就给你便宜点啦”
,麻利地找来租约。
最终,顾远以每月两千块的价格,拿下了这个四十平米的单位,比市价略低一些。房东太太收了钱,眉开眼笑,连带着看李晓红的眼神都和善了几分,大概是把她当成了顾远那位“有钱表哥”
带来的亲戚。
搬家很简单,两人本就没什么家当。添置了些必要的家具和日用品后,这个临时的“家”
总算有了点样子。李晓红有了一个带小窗的房间,虽然不大,但足够她摆下一张单人床和小小的梳妆台。看着她小心翼翼整理自己那几件旧衣服时眼里的光彩,顾远觉得这两千块月租花得挺值。
有了相对安稳的环境,顾远再次投入到“资料库”
的搬运工作中。剧本大纲、分镜头草图、新的歌曲旋律……他需要尽快将脑子里的东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本。李晓红则继续承担起后勤部长的职责,买菜做饭,打扫卫生,将这个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之前的平静,只是空间更大了,彼此也更自在了一些。
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顾远难得放下笔,和李晓红一起去附近的街市买些东西。香江的午后依旧炎热,街上人来人往,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和生活的气息。
走着走着,一阵略带沙哑却饱含深情的歌声,伴随着熟悉的旋律,从街边一家售卖磁带的小店里飘了出来。
“……爱过,痛过,眼泪,干了……”
是《遥远的他》。
顾远脚步微微一顿。
距离录音棚那天,刚好过去半个月。豹哥的效率看来还行,这么快就把单曲铺出来了?虽然只是街边小店在放,但这无疑是个信号。
李晓红显然也听出来了,她惊喜地看向顾远,眼睛亮晶晶的:“顾大哥,是……是阿友哥唱的那首歌!”
顾远点了点头,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,心里却在快速计算。这种街头巷尾的自然传播,比电台硬推有时候更能说明问题。这首歌的潜力,看来比他预想的还要好一些。
李晓红看出了顾远似乎想了解更多,她犹豫了一下,然后鼓起勇气,小跑着到那家磁带店门口,用她那依然蹩脚、带着浓重山东口音的粤语,跟看店的小伙计比划着说了起来。
顾远站在不远处,看着她努力沟通的样子,嘴角不由勾起一丝浅淡的笑意。这个姑娘,虽然胆子小,但关键时候却很懂得为他着想。
聊了好一阵,李晓红才红着脸跑回来,有些兴奋地对顾远说:“顾大哥,那个小哥说,这首歌最近好多人听,好多人问!他自己也很喜欢听,说唱得很有味道,听了心里酸酸的。”
“嗯。”
顾远应了一声,心里有数了。
两人继续往前走,没过多久,又听到路边一个拿着便携收音机的大叔,也在播放着《遥远的他》。甚至还有年轻人,用那种方块状的录音机,把电台里播放的歌曲录下来,反复播放。
看来,这首歌是真的开始发酵了。顾远心想,离“红”
,确实不远了。至少,阿友这个名字,很快会被越来越多人记住。而作为词曲作者的他,虽然暂时隐于幕后,但价值的天平,已经开始悄然倾斜。
傍晚时分,两人提着买好的菜回到楼下。刚走到楼梯口,顾远就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等在那里。
豹哥斜靠在墙边,指间夹着一支烟,烟雾缭绕。旁边是阿友,依旧是安静的样子,坐在楼梯台阶上,眼神有些飘忽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“豹哥,阿友。”